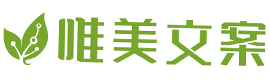这是个月牙高挂繁星闪烁的夏夜。
汾河岸畔并州城迎宾大道旁,喇叭花似得路灯洒出桔黄色的灯光,照射着大道上各种牌号的车辆,这些车辆从东往西从西往东,转动着轻快的车轮驶向前方。
路两旁,树荫下。三三两两的市民坐着马扎端着水杯,在凉爽的晚风中悠闲消遣着这迷人的夜晚。
然而,一位中年女士丁兰却不悠闲,她骑着电动自行车,双手紧攥车把,顶着风,把车骑得风驰电掣一般,在自行车的洪流中冲向前。
她额前的黑发被刮起,露出饱满光洁的额头,一双漂亮的凤眼一眨不眨地直视前方。
自行车到市文化宫大门,她车把一拐进了门,超过院中正在准备往停车场走的车辆,骑向存车处,存好自行车。急冲冲奔向闪烁着霓虹灯大门的台阶。
台阶上站着许多人。他们有人是准备进文化宫看电影,有人是准备去游戏厅娱乐。更有一些衣冠楚楚,修饰干净的男士女士是准备进舞厅跳舞。
丁兰走上台阶,在一个角落从身上挎着的包中掏出手机,拨通号码:“喂,淑华,我来了,你在哪儿?”
“我在里面,你进来吧。进了门朝左走,注意,别让你老公看见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丁兰关掉手机装进包里。从包里拿出一副眼镜戴上,她把散乱的黑发扎成马尾辫,轻轻整理了一下身上的黑色半袖连衣裙,踏着碎步到售票处买下票进入舞厅。
舞厅里灯光幽暗,朦朦胧胧,人影绰绰。
舞厅顶上有一盏转灯在慢悠悠的转,放射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。墙壁上的霓虹灯闪闪烁烁,把舞池里正在跳舞的一对对男女脸上照射的或明或暗。
丁兰站在门口一个个头高大的男人身后。刚进来,眼睛还不适应舞厅里的黯淡光线。她等了会儿,睁大漂亮的眼睛,朝舞池中跳舞的人们扫视几眼,然后沿着舞池边朝左边走去。
她来这儿是找人,找丈夫李本天。
三天前。密友赵淑华对她讲,李本天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小舞伴,两人经常在文化宫舞厅跳舞。她不相信,李本天笨的跟个驴一样,还能跳舞?
可赵淑华说的有鼻子有眼,还说你不信就到舞厅去看看。她知道赵淑华常去舞厅跳舞,还有个舞伴叫孙二桃。
两人天天泡在舞厅,可能是见过她老公。所以她半信半疑。跟着赵淑华到了舞厅两次,可一次也没碰上李本天。
今晚她不想来,可没想到赵淑华打来电话,说李本天和他舞伴到了,她相信了。
因为半个小时前,李本天离开家,走时告她去战友家搓麻将。是搓麻将还是跳舞?李本天不在家是肯定的。
怀着疑惑的心情,她在舞池边上走了一截儿,没找到赵淑华,也没看到李本天。舞池中人太多,一对挨着一对,一个比一个打扮的俏皮,一个比一个穿戴潇洒,扎眼又引人注目。
而李本天那个笨驴,走时穿的是件红格衬衫黑裤子,不好找。
她找了个光线黯淡的角落,站在那儿左顾右盼,时不时还去瞅舞池中一对对扭腰转动的男男女女,没料到身后站了个人,凑到她耳旁:“兰兰,看到没有?”
她知道是谁,没动身,只扭头看了眼,焦虑的说:“淑华,这么多人,哪儿看得到他?”
“别急。在哪儿了。”赵淑华抬手朝舞池中另一边指去,边指边说:“我早看见你了。
刚才你过去的时候,你老公正在雅座上和那小妮子闲聊,你没看到他出来跳,快看,那儿。”
丁兰顺着赵淑华的手指望去,看到老公李本天搂着一个身段苗条,梳着小辫的女的正热烈跳动。
她心里腾地冒出股火气,怒气冲冲的骂:“好个你李本天,搓麻将搓到舞厅来了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抬脚准备过去,赵淑华忙拉住她的手:“别去,等等。”
“等啥?”
。赵淑华头伸过来,低声耳语:“你过去能说啥?人家是跳舞,又不是胡搞,你这不是打草惊蛇。”
说罢,把丁兰拉到身后的一把椅子上坐下,“等一会,戏演开你再过去”
“还有戏?”丁兰自言自语。她只好坐下,压住火气去细细观察,她要看看同丈夫勾挂的女人是妇人还是姑娘。
那女的圆脸大眼,头发浓黑,小辫上扎着蝴蝶结,短裙黑皮鞋,裙子下露出一双坚实的小腿,细腰尖臀,显得俏皮活泼。
从身腰上看应该是姑娘,不是结过婚的女人。
舞曲停,人们向四周散去,李本天拉着那个小姑娘的手朝这边走过来,丁兰赶紧低下头,心想:他要看到我了。
但又一支舞曲很快开了,李本天和那姑娘勾肩搭背又进了舞池。忽然,大厅里的灯熄了一半,很快又熄了一半,只剩下屋顶上的一盏转灯,慢悠悠地转,放射出暗淡的光线,大厅里变得很暗。
舞曲是慢四步,布鲁斯,草原情歌《敖包相会》。这支舞曲音域宽广,优美动听,令人心情荡漾,愉悦兴奋。
李本天和那个姑娘相拥在一起,踩着鼓点慢慢晃悠。
丁兰刷的站起,心里生出一种感觉,觉得那两人要有事,因为此时舞厅里已变得漆黑一片,可说伸手不见五指,那支转灯是个摆设,还不如天上的月亮明。
但赵淑华又拉住她的胳膊说:“再等等,一会儿他们肯定有戏。”她站住不动,沉默不语,心里却似乱麻一般,不安的很。她双目紧盯李本天,生怕丢失目标,
时间长了,屋顶上的那盏七色灯似乎也有了点作用,虽说是慢悠悠的转,放射出来的那点灯光还是能看清舞池中一对对的舞侣。
他们有的是搂脖子搂腰,像两根电线杆儿并在一起,有的是在原地晃悠,像风中的小树摇摆,有的是走大步,跳标准的国标。舞池里面朦朦胧胧,人影绰绰。
丁兰没有丢失目标,虽然舞池里又增加了几十对舞侣,人们在晃动,人影错位,但李本天是丢不掉的,她熟悉丈夫的体型,突然,赵淑华推了她腰上一下:“快去,他们在搞小动作。”
恰巧,转灯的一缕黄色光线射到李本天的大鼻子和那个姑娘的脸上。
顿时她怒气冲天,三步并作两步扑到李本天跟前,一把抓住那个姑娘的肩膀,使劲往外扯,同时大骂:“好啊李本天,搓麻将搓得跟一个姑娘搓到一块了,真不是个东西!”
那个姑娘被扯到一边,丁兰朝李本天脸上狠狠打了一耳光,两只手伸上去抓他的脸。
丁兰的怒骂使舞厅大乱,顿时响起一片吵吵嚷嚷叽叽喳喳的声音:“怎么了?”
“打架了”
“谁打谁?”
“老婆打老公?还是老公打老婆?”
人们纷纷朝四周躲去,担心打架的人出手乱打,黑乎乎的看不清你我,打住自己不是白挨?
躲避的人互相撞在一起,被撞的人恼火的乱骂,有的女人被踩了脚背,大声尖叫;
有的男士寻找女伴,拉住别的女士的手腕,被人家责备几句:“乱抓什么!”闹得怪没意思。舞池里乱哄哄一团
李本天在听到的骂声后,听出这骂声是他老婆丁兰的声音,是来找茬儿,他站住不动。管理人员在听到舞厅里人们混乱骚动的嘈杂声后,忙停了音乐合上灯闸。
霎时间,舞厅里灯火辉煌,亮如白昼。李本天呆楞的站在舞池中间,他之所以站着不动,是在等他的舞伴林小雪。
灯亮后,他定睛一看,林小雪已没人影,站在他面前的是丁兰。而丁兰已踮起脚后跟,又伸出手去抓他的脸。他气恼的大吼:“胡闹了你!”他不敢打丁兰。
他在部队练过武术,在师里拿过散打冠军,一出手就会伤人,只敢抬起胳膊阻挡一下。
但没起作用,丁兰的双手还是在他脸上狠狠抓了几把,他感到脸皮火辣辣的疼,不由得抬手,一掌推向丁兰的胸前。
“扑通”一声,丁兰被推倒在地板上,屁股跌得生疼:“哎呀,妈呀”的失声大叫,她两脚在光滑的地板上乱蹬,扯起嗓门大嚎:“李本天,你敢打我!你个没良心的家伙!
乘此机会,李本天气呼呼的扭身走了。
赵淑华始终没敢往前凑。她怕李本天知道是她告的密,以后找她的茬儿。看到李本天走了,她才过去拉起丁兰的手:“起来吧,你家老李走了,咱们回吧。”
赵淑华的舞伴孙二桃也走过来,拉住丁兰的另一只手,细声细气的说:“兰姐,咱回吧,回去收拾你老公。”
丁兰一看孙二桃,心里就来气,她手一甩:“不用你管!”她对赵淑华的这个舞伴有很深的看法,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说话走路都是一副女人相,扭扭怩怩,哪像个男子汉,跟哪儿学的?
可偏偏赵淑华就喜欢他,宁和丈夫闹离婚,也要和孙二桃同居。她和赵淑华要不是老同学,早就断交了。
孙二桃的话刚落,从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两人,一男一女,是舞厅的保安。两人伸出手,女保安扶住丁兰的肩膀:“大姐,别坐着了,你老公已走,回去找他算账。”
丁兰的身子动了下,感到臀部生疼,浑身没劲。可能是刚才打李本天,过于着急把劲儿全使完,她“哎哟哎哟”呻吟几声:“我起不来了,骨头断了。”
“能断了骨头?净胡想。”赵淑华握住丁兰的手把她往起拉。
“我来扶你。”男保安站在丁兰身后,伸出双手,弯腰扶起她的双臂,用劲把她抱起来:“回哇,回去收拾他,大姐,找个鸡毛掸子把他打到床底下。”
“就是,他可能已回了家。”赵淑华说。
是的,他可能已回了家。丁兰也这样想。
不知怎么,她突然来了精神,臀部也不觉得怎么疼了,骂道:“你从这儿跑了,能跑到哪里?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,我回去收拾你。”
丁兰站起来,一瘸一瘸,跌跌撞撞的往外走。舞厅里的灯光刷的一下又全部熄灭,霓虹灯开始闪烁,音响里传出舞曲,人们又欢乐的跳起来。
丁兰和赵淑华、孙二桃走出舞厅的门。下台阶时,天空上一道闪电,“咔嚓”一声,一个闷雷在头顶上炸响,豆大的雨点从天上落下来。
赵淑华说:“不要骑你那个破电动车了,咱们打的回。”
丁兰说:“好的。”
三人急急忙忙往台阶下走。不料,在下最后一个台阶时,丁兰脚一软,跌了一跤,臀部又跌的生疼。她“哎呦”一声:“我倒了霉了,这个李本天害苦我。”
赵淑华却乐呵呵的笑:“你回去好好的调教他。”
孙二桃跑到路边拦出租车。
在车上,赵淑华问:“你回去怎么收拾他?”
丁兰沉吟了下:“我还没想好怎么收拾他?你说有什么办法?我都不知该怎样。”
赵淑华说:“让他跪下给你认错。扇他几个耳光,好好的教育他,不调教好不要罢休。如果他敢还手,你就和他离婚。”
“他不敢还手。他要敢打我,让我爸我哥知道了,非打死他不可。”丁兰不屑地哼了声。
“还是你有福,有个当官的老爸当官的哥。”赵淑花充满羡慕。之后问,“他要是不和你过了?提出离婚,咋办?”
“由他了!他倒厉害。我不离。”丁兰冷冷的说。
“是吗?你觉得还能凑付着过?”赵淑花盯住丁兰的脸看,看了会,她长长“噢”了声,似乎醒悟:“想起来了。是不行,不能离。”
“什么行不行?现在谁离了谁都行。”孙二桃在副驾驶座上,扭回头不冷不热的说。
“乱说个什么?闭上你的嘴!”赵淑华狠狠地斥责。
丁兰也不满地朝孙二桃瞪了一眼,心里骂,你懂个屁!她想起件事。
两个月前。有天傍晚,她受赵淑花的邀约到文化宫舞厅玩,准确的说,她是去看热闹,可不是去跳舞。
她对交谊舞看不惯,认为男的和女的勾肩搭背拥在一起不好看。这位曾经的女大学生为什么会看不惯交谊舞?这与她小时候听到的一些事有关。
那是她6岁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。妈妈领着她,和院里几位阿姨到附近的一个灯光露天舞场看跳舞。
那些阿姨都是随军家属,有些是从偏远山区来到部队,没见过跳交谊舞,听先来的阿姨讲附近有舞场,便相约去看跳舞。
她们站在栏杆外面,从栏杆中朝里面看。跳舞的人很多,几乎全是年轻人,他们一个个洋溢着快乐的表情,使劲地跳啊转啊。
对这种脸儿相近,手儿相握,腿儿相挟的男女共舞,她看不出什么,只有些好奇。在幼儿园,她每天和小朋友拉着手跳集体舞。
可这些叔叔和阿姨们是抱在一块跳。他们个个都显得愉快高兴,显得那么亲热友爱。让院里的阿姨们看出名堂。
一位阿姨对她妈说,你看那一对抱得好紧,肯定他们关系不正常。妈妈也说,就是,我看也不正常。跳就跳罢,抱那么紧干啥?
又一位阿姨故意夸张地说。不是。另一位阿姨认真的讲解,我早看清了,他们是在说悄悄话。顿时,阿姨们响起一阵会意的笑声。
笑声过后,又一位阿姨说,一位阿姨笑说,媚惑男人呗。一下子阿姨们又都乐呵呵的笑起来。
笑声中,一位阿姨指着栏杆里一对正在做动做的舞伴,你们瞧瞧,那两人生气了,看,女的要走,男的拉住女的手不让走。
俺们村小俩口闹架也是这个样,这跳舞也闹这个,逗人得哟。丁兰去看,果然是阿姨说得那样,女得身子向前倾斜,脸也朝前,胳膊向前伸得很长,就是要走。
后来她听别人讲解,那是中四步中的一个花样动作,叫探海。
当时她却认为,那两人是夫妻俩口子,女的不想跳了,男的不让走。阿姨们说来说去,一致认为那里面“好东西”不多。
从那时,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对交谊舞留下很不好的影响,也认为那里面“好东西”不多。
上了大学,她对交谊舞有了新的认识。学生会举办舞会,她经常和舍友一块去看。刚开始,她主要是看那个男生对那个女生献殷勤,是不是想同人家谈恋爱。
后来,看得多了,她也认为交谊舞是文明的像征,有益社会交际。但她还是不愿跳,进了舞厅,心里时时有句警语,我不当“坏东西。”
那么,赵淑花是“坏东西”吗?不是。她俩从初中到高中在一个班学习,彼此了解。赵淑花是个热情乐于助人的人。
因她生性孤傲,在班里受到女同学的孤立。赵淑花主动接近她,帮她排忧解难。这样的人能成坏东西,鬼都不信。
可赵淑花偏偏喜欢上“坏东西”们做得事,陷泥坑而不拔,除上班连家都不顾,每晚在舞厅和孙二桃鬼混。
说赵淑花和孙二桃在舞厅鬼混,一点都不冤枉她,是因为她有老公,还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儿子。背着老公和其他男人不是鬼混是什么?
她想责备赵淑花几句,又觉得干涉人家的私情不好。再好的朋友也有私情,不问最好。
丁兰对孙二桃十分看不起,嫌他说话细声细气,走路扭扭捏捏,缺乏男人味。他为啥叫女孩子的名字?桃红柳绿,想来可笑。听说他上面有个哥。
当年他妈生他的时候,想要个女孩,结果是个男的,就给他起了个女孩的名字,把他当女孩养,小时候还给他穿过花裙子。
他呢,慢慢地也有了女性特征,走路扭扭捏捏,说话细声细气,让人看着就觉得怪气。可没办法,这个阴阳人是赵淑花的相好,两人正商量着结婚,她还得帮赵淑花的忙。
也真奇怪,赵淑花都38了,怎么能和一个26岁的小后生好上?她问过几次,你为啥和他好?赵淑花总是笔咪咪的说,这是私秘。私秘就不告诉老朋友了?
她生着气责问。赵淑花不停的向她倒歉,就是不说原因。
丁兰想,赵淑花有什么私秘瞒她?为啥硬要同丈夫打架吵嘴离婚?
离不了婚就和那傻小子同居?结果呢,闹得北钢人人皆知,都议论一轧厂出了对少夫老妻,臭名远扬。
他们是怎样混到一块的?有人说,是跳舞,他俩每天晚上在舞厅跳,这种说法丁兰认为说得对。赵淑花喜欢跳舞,可说是天天晚上都去舞厅。
以前有过几个舞伴,交往时间都不长。就这个孙二桃,和她粘到一块不放了,从舞厅开场到关门,两人热乎的难舍难分。
丁兰有意识跟赵淑花去了几次舞厅,想看看她和孙二桃在干什么?舞厅有什么魔力吸引她。结果是她也差点跌进去。
那次,一位温质彬彬的中年男士请她跳舞,往常她是不会站起来,摆摆手就拒绝了对方。
这次她一时心血来潮,站起来说,我不会跳。男士说,没关系,我来教你。她就站过去了。当她的手被男士握住时,心咚咚直跳紧张得很。
而跳完后,她心里却产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愉悦,时时幻想有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抚摸她,吓了她一跳,这是种扭曲心理,可不敢学了。
而赵淑花和孙二桃进了舞厅真是如鱼得水,像回了自己家一样,俩人啥舞都跳,啥动做也敢做。
别人不敢在舞中亲吻,她俩敢,真不害羞。就不知有多少双眼在蔑视。
丁兰认为,赵淑花和孙二桃结不成婚,是因为赵淑花的丈夫,一个老实巴交的成型工坚决不离婚。虽然赵淑花和丈夫又吵又打,把丈夫的耳朵拧肿也没离成。
孙二桃想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和他的身份证。他妈把户口本和他的身份证藏到一个世界上最秘密的地方,最高级的侦探也找不到。他妈还到厂里,请求厂领导阻止他们结婚。
厂长把孙二桃叫去,把他骂了个灰头土脸,最后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,厂里不干涉你的婚姻自由。
可你要明白,等你40多的时候,那女的跟你妈现在一样,老迷疙皱,而你还是英俊小生。你看着办吧。
但孙二桃还是和赵淑花在外边租间房子同居。
孙二桃的母亲,丁兰见过。是位50多岁,圆脸富态慈眉善目的老妈妈。
记得那天傍晚,她文花宫舞厅时,舞厅门前已站了一些人在等着开门,她看到赵淑花和孙二桃坐在门前台阶上的水泥护栏上,一人手中拿着一瓶饮料正嘻嘻哈哈的说笑。
赵淑花见她来了,对孙二桃说:“给兰兰买瓶饮料去。”孙二桃愉快的答应:“好地,花姐。”从栏杆上跳下来准备去。
突然孙二桃着急地说:“不好,我妈来了。”跟着又一句,“我爸也来了。还有我嫂子。”他一声高过一声,慌得不知朝那去。
孙妈妈已走到台阶下边,挡住儿子逃跑的路。台阶上已没路可逃。孙二桃跑到侧面栏杆处,可看到栏杆与地面有一丈多高,他不敢往下跳,只好返回来。
赵淑花也从栏杆上跳下来,一把拉住孙二桃:“快蹲下。蹲在我身后。”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,把孙二桃遮在自己的臀部后面。
丁兰幸灾乐祸地说:“蹲下顶啥用?他妈早看见了。快起来,别丢人败兴。”
确实,台阶上站着许多人,都在笑呵呵的看。
孙妈妈仰着脖子朝台阶上凄楚的喊:“二桃。跟妈回家吧,二桃……”这喊声中充满苍凉悲哀。刹那间,看热闹的人们都收敛笑意,盯住孙二桃。
孙二桃蹲在赵淑花身后,探出头朝台阶口看。他妈和他嫂冲着赵淑花奔过来,他呼地站起,朝旁边的几个人身后躲。
那知他妈的眼睛跟扫瞄仪一样灵,紧盯住不放,“二桃,跟妈回家。”气喘吁吁的孙妈妈流着泪喊,大概是跑得急,声音低了许多。
那几个人哗啦一下有意识地让开,把孙二桃晾在光天化日下。孙妈妈疾步过去。赵淑花急了,迅速挡在孙妈妈前面。
孙妈妈怒气冲冲地责问;“你什么人,挡我的路。”
赵淑花不吭声。孙二桃说话了:“妈,她是我的女朋友。”
孙二桃的嫂子冲过来,朝赵淑花胸前推了一掌;“滚开!好狗不挡道!”
“你骂谁?”赵淑花听到对方骂人,她得了理,理直气壮地抓住孙二桃嫂子的肩膀责问,“为啥骂人?”
这时孙妈妈已反应过来,明白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勾引她儿的妖精,抬起手朝赵淑花脸上打;“骂人?我还要打你了!妖精!”
赵淑花抬起胳膊挡住,朝孙妈妈肩上打了一下。孙二桃看到,大喊:“花姐,不敢打,她是我妈。”
赵淑花才不管谁妈。和孙妈妈扭扯到一起。你抓我一下,我打你一下,谁也不让谁,谁也不往后退,谁也不甘示弱。
孙二桃的嫂子见此状态,抱住赵淑花的后膘往后拖,可能是想把赵淑花拖倒。
赵淑花受到限制不能发力,急得去掰孙嫂子的手,掰不开。孙妈妈乘此机会在赵淑花的脸上乱抓,她每抓住一次,赵淑花都疼得啊啊叫,她白皙的脸上出现一道道指甲印。
“妈,别打了,饶了她,”孙二桃站在中间伸手拉他妈,“妈,她是好人,放过她。”
“好个屁!”孙妈妈停住手,气呼呼的责骂儿子,“好姑娘可多了,你非要和这个大你十来岁的妖精混在一起,给老孙家丢人败兴!”
孙二桃的爸爸上来了,一把抓住孙二桃的手腕,扬起胳膊朝儿子脸上“啪啪”就是两巴掌:“混账东西,给我滚回去!”
孙二桃一看是老爸,他脖子一挺,用劲往开甩手,硬生生地顶:“不回,就不回!”
孙爸听了儿子的话后,火冒三丈,抬手又是一巴掌:“反了你!还就不回了你。我看你就不回。”说着,连朝儿子头上打了几掌。
丁兰见此,觉得她能管了。上去拉住孙爸的手:“叔叔,不要打人,打人不好。有话说清楚,讲道理。”
孙爸爸见出来一个多管闲事的女人,气得糊涂,一甩胳膊,抬手朝丁兰推了一掌:“去,一边凉快去,吃饱了撑得没事干,管我的事。”
丁兰何时受过这种轻视,不由得生气。她又拉住孙爸的胳膊,口气坚决:“打人不对。不能打。”
孙爸又一甩胳膊,吹胡子瞪眼地责问:“我打他咋啦?他是我儿,老子打儿子,天经地义!”
丁兰还要再说,听到台阶下传来一声大喊:“住手,不准打架!”她去看,是哥哥丁建和警官高国顺,两人一步两个台阶往上奔。
孙妈妈和孙爸爸,还有赵淑花和孙嫂,四人停住了手,谁敢在警察面前继续打斗,肯定处罚的谁重。
丁建到了他们几人面前,严厉责问:“为什么打架?”
几人面面相觑,谁也不吭声,刚才那杀气腾腾的劲头眨眼间跑到爪哇岛上。
“为什么打他,问你了?”丁建盯住孙爸。
“他是我儿。他不回家,在外边胡混。”孙爸嘴唇嗫嚅,不愿多说。
“他不回家你就打他?”丁建问。
“是,不听话,不打能行?。”孙爸理直气壮地反问。
“不听话,你也不能打。打人是违法。”丁建说。
“他是我儿,我管教他不行?”
“你儿你也不能打。打是家暴行为,要负法律责任。”丁建严厉呵斥。
孙爸不吭声了,垂下头躲开丁建的目光。
丁建转过脸问赵淑花:“你是怎么回事?”
赵淑花指着孙妈妈:“她打我。你看我的脸都被她抓破了。”
丁建看着赵淑花俊俏的脸上一道道的指甲印,问:“她为什么打你?”
“我和她儿谈恋爱,她思想落后,反复阻挠我们来往,还来这儿打我。”赵淑花说得振振有词,合情合理。
这时,孙妈妈着急了,慌里慌张地说:“警察同志,不要听这妖精胡说,她咋不说她多大,我儿多大?
她比我儿大12岁,38的人了,有了老汉和儿子的人,还非要找我儿。她是看我儿长得好看,就勾引他。妖精!”
“不要骂人。”丁建制止道,他明白了,这就是北钢工人流传的少夫老妻的那个女人。这件风流韵事传得沸沸扬扬,不但北钢的人知道,就连市里的有些人也知道。
对他们女大男小年龄悬殊的婚恋感到不可思议。中国的婚姻传统观念是男的比女的大几岁,也有的地区是女的比男的大个一两岁,或者三岁。
称谓女大一有福气,女大二儿女全,女大三抱金砖。说得都是女的比男的大的好处。可这大12岁有啥好?没法说。
只能把他们请到派出所了。他严肃地说指出:“你们在公共场合打架,是扰乱社会秩序,我请你们到派出所谈话。”说罢,他朝大门那边挥了下手。
一辆警车稳稳地开进来,停在台阶下边。一名警察从车上下来,站到车旁。
警官高国顺对众人说:“请吧,到派出所去学治安法。”
孙爸和孙妈在犹豫。赵淑花毫不在乎,她先抬脚朝台阶下走,响起一串沓沓沓匀称的脚步声。
孙妈下个台阶歪下身,步子不稳。孙二桃的嫂子赶紧上去扶住。婆媳二人走下台阶。
孙爸还是紧紧拉着孙二桃的手往下走。孙二桃几次想挣脱,就是脱不开。
丁兰站到丁建身旁:“哥,我也去吗?”
“你不用去。”
“哥,淑花是我同学。”丁兰指着台阶下的赵淑花。
“认出来了。你给我说过她的事。”
“你怎么处理她?”
“谈过话后放她走。主要是让她学习社会治安法。以后不要在公共场合吵嘴打架。她谈恋爱的事我们不管。不过,要给她个提醒,不要胡来。他们年龄上有些悬殊,说法太多。”
“哥,你也是这种认识,认为少夫老妻不好?批评他们不要相爱。”丁兰不满地嚷嚷开,“中国就这通病,只能有老夫少妻,男的比女的大个十几岁,二十几,三十几的有之。
而只出了这么一件女的比男的大十来岁的婚恋,个个就大惊小怪,嚷嚷不休,仿佛天要塌了,太不公平了。”诚然她对孙二桃鄙视在心里,可她要为赵淑花辩解,抱打不平。
“你不要管闲事。回家待着。”丁建皱起眉头责备丁兰。
“不。哥,”丁兰不高兴的嘟囔,她在哥哥面前从来都是想说什么说什么,“淑花是个好人,为人直爽,乐于助人。就是有个毛病,喜欢跳舞。都是跳舞惹来的麻烦。”
“不要怨跳舞。喜欢跳舞的人可多了,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各种人都有,人家就没有像她那样非要离婚找孙二桃?他俩碰到一块,管不住自己就瞎胡来。”
“这不就对了,还是跳舞让他们结识,跳舞让他们粘合到一块。哥,咱们认识不一样吗?”
“也可能是,”丁建急得要走,顾不上和丁兰多聊,但他还是说:“不要怨跳舞,是他俩都有那方面的想法就走到一块了。”
“什么想法?”丁兰不解地问。
“想胡来的想法。”
“是吗?”丁兰疑惑地思索。
“你好好想一想。我得走了,以后再说。”丁建摆摆手,急匆匆朝台阶下走去。
望着哥哥的后背,丁兰不满地发牢骚,想什么?他们不是跳舞能认识吗?还不要怨跳舞?哼!就是跳舞的问题。
那天的认识,今晚丁兰又得到印证,她在舞厅抓住李本天和一个姑娘鬼混,真让她怒火冲天气!
得好好考虑考虑。现在该怎么办?万一他要是提出离婚,离不离?自己有难以启齿的病,这个病让那些的女人听到会笑话,你怎么得了那种怪病?
这个病也可能是造成李本天在外面寻花问柳的借口,他要是说出去对她不利。当然她的病不是看不好,肯定会看好的。
问题是离了婚,李本天马上就能再婚,跟新欢去度密月。她呢?
都快40的人了,去那找?再说近几年,因为这个病压得心力交瘁,经常失眠,心情不好,相貌苍老许多,成了残花败柳,就是看好病还有谁愿要?
所以不能离,把他哄回家?这是件麻烦事,现在还不知他听不听她的话?都是他的错,回去找他算账。
丁兰回到家门前,见家门紧闭,她不从包里拿钥匙,也不按门铃,而是朝门上踢了几脚,“嘭嘭嘭!”
这个在营房里长大的女子,性格直爽急躁。她踢门,是要让李本天知道,她回来了,给她开门!
屋里传来一串脚步声,“咔哒”一声门开了,儿子乐乐站在门口,仰起圆圆的小脸,露着诧异的眼神:“妈妈,你回来了?”
丁兰没同儿子说话,急冲冲走到客厅去看,沙发上没坐着李本天,她又推开卧室门,卧室里黑着灯,她按下墙壁上的开关,灯亮了,床上没人,显然李本天没回来。
乐乐在她身后跟着,她扭身问:“你爸没回来?”
“爸爸没回来,妈妈你怎么了?”乐乐对妈妈的满脸怒气觉得奇怪。
丁兰没回答儿子乐乐的问,走到客厅沙发上坐下,两眼茫然的扫了下电视屏幕。上面正演孙悟空拿着金箍棒大闹天宫。
儿子在看电视,完成作业没有?她顾不上问,心里还在想:李本天,我等着你,你什么时候回来,我什么时候跟你干!
她掏出手机,准备给哥哥丁建打个电话。万一要是打不过李本天,就让哥哥来帮她打。
她能打过李本天吗?肯定是打不过,她要做个准备。以前她同李本天打架,李本天从不还手,顶多抬起胳膊挡一挡,大声嚷嚷几声。今晚却给了她一掌,没良心的东西
按完号码,她没按通话。心想,李本天敢还手打她?她可是没做错事!。勾搭女人胡搞是他李本天,是他应该挨打。
用什么打?她的眼睛在客厅里转了一圈,没啥顺手东西,茶几上放的是乐乐的作业本。她去看乐乐。
乐乐是个聪明的孩子,在班里学习成绩总是在前三名,让她骄傲,可她回来这么长时间,却没问他一句。
她长喘口气,静下心,思考了会:“乐乐,作业写完了吗?”
“写完了。妈妈。”
“开了学要上三年级了。这个署假你到姥爷那儿去住。让姥爷领你去补课。”
“嗯。妈妈,我听你话。”乐乐轻声回答,显得很乖。他是见妈妈满脸怒气,便知道妈妈和爸爸又吵嘴了。
在他脑海里,记录着妈妈和爸爸经常在半夜三更吵嘴,有时还打几下。他依偎到丁兰的怀里,摸住她的脸颊,发着稚嫩的童音:“妈妈,你和爸爸吵架了?”
对儿子的问,丁兰不吭声,她垂下头想,儿子这么懂事听话,不能说他爸胡来的事。
乐乐见妈妈不说话,就摇摇丁兰的胳膊。丁兰仍不吭声,肚里闷着一肚子气,想往外发又说不出来。
乐乐见妈妈总是沉默不语,便学着哄人:“妈妈,你喝水不?”说罢,跑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水。水接的满了,他双手端住,小心翼翼走到丁兰面前,边走边说:“妈妈喝水,喝水。”
丁兰见儿子端水过来,她正口渴,赶忙伸手接过来喝了一口,一股清澈凉爽的水似甘露一般从嗓子流进心田,扫去她心底的一些烦躁。
她咕噜咕噜几口把杯子里的水喝净。
看着儿子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在仰望她,她心里一阵辛酸,凄楚,说不清怎么回事,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,“哇”的一声哭了,她伸手把乐乐抱进怀里,边抽泣边说:“你爸爸坏呀,不是个东西,胡来。”
“妈妈,爸爸打你了?”乐乐怯生生的问。
丁兰没吭声,对儿子的话她真没法回答,总不能告他,他爸在外面搞女人,让她抓住了。这会让他心里难受,让他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。这种事是不能让儿子知道的。
“妈妈,爸爸打你,我打他。”乐乐一副男子汉的口气,伸出一只小手捏成拳头在丁兰的眼前晃了晃,又去轻轻摩挲她脸上的泪珠。
儿子稚嫩的声音、轻柔的动作、大气的语言,使丁兰心里悲哀的很,她不由得大声哭起来,身子随着哭泣剧烈颤抖。
乐乐被吓着,也跟着哭。他摇晃着丁兰的胳膊,不停地说:“爸爸坏,妈妈打他。”
丁兰见儿子这样替她说话,心里生出一丝温暖,她把乐乐紧紧抱在怀里,轻吻他的小脸蛋。
心想:跟他离婚,有儿子乐乐留在身边就行。她喃喃自语:“宝贝,你爸爸是个坏东西,不懂事,你长大后可千万不要学他。”
乐乐擦去眼窝中的泪水,哽咽着问:“妈妈,爸爸做了什么坏事?”
这可把丁兰问住了,怎么回答?告不告?告,不好,不告,又觉得憋屈。想了会儿,她无可奈何的叹口气:“乐乐,别问了,妈妈以后再告你。”
“嗯。”乐乐懂事的点下头。
丁兰轻轻抚摸着儿子头上的黑发,心里酸酸的发胀,她强忍住又要淌出来的泪:“乐乐,明天妈妈就送你到姥爷家,带上书包,不要见你爸爸了。”
乐乐仰起脸,瞪大他明亮的眼问:“妈妈,是不是你和爸爸又成了好朋友,我才能见他?”
“嗯。可能是吧。”对儿子天真的问,丁兰心情沉重又无奈的回答。现在该怎样处理李本天这件丑事,她还不能做最后决定。
毕竟她和李本天已经结婚十年,有一定感情,还有个儿子。急急噪噪的提出离婚,不给悔改的机会,合适不合适?
“妈妈,要不要我帮你的忙?”
“帮什么忙?”丁兰被打断思考,茫然的问。
“打坏蛋爸爸!”乐乐伸出拳头在空中挥舞。
丁兰苦笑了下,无力而又困难的说:“宝贝啊,你还不懂,等你长大了,懂得了再说。现在睡吧,在妈妈怀里睡。”她摸住乐乐圆圆的后脑勺:“睡吧,宝贝,宝贝。”
没一会儿,乐乐睡着。丁兰轻轻抱起乐乐,往卧室里走,她感到儿子又重了些,有些抱不动,但她还是把他抱在怀里,放到卧室的床上,轻轻脱去他的鞋和裤子。
拿了条毛巾被给他盖上。看着儿子发出均匀的呼吸,她长叹口气,躺到儿子身边。
一会,她感到身上袭来一阵疲倦困乏,仰脸看了眼墙上的挂钟,已过午夜12点。
这一眼看的她,身上虽乏却没了睡意,瞪大双眼看屋顶,她要等李本天回来,问个长短。
时间飞快流逝,到了1点多,夜静人稀,能听到马路上车辆驶动的声音,却还听不到有人踏楼梯的脚步声,李本天不回来了。
她从床上下来,蹑手蹑脚走到卧室门旁关了灯,出来,关住门走到沙发前坐下。呆愣的想,李本天肯定是不回来了。咋办呀?
要是能和一个人说说,看看她们的说法就好了。和谁说?赵淑华?她拿起手机。可没想到来了电话,是赵淑华打来的。
“怎么样,兰兰,你老公打你没有?”
“他就没回来。我正想着该怎么办呀。”
手机那头赵淑华问:“什么怎么办呀?你不是不想离婚吗?”
她说:“我是不想和他离婚。可要是宽容了他,也太便宜了他。至少也要让他给我写封认罪书,以后改邪归正,不再勾搭人家女孩才行。”
“是这么回事,不能轻易饶了他。他要不认错,你就和他闹。”
丁兰问:“怎么个闹法?我现在心里空荡荡的,不知该咋办?”
“不要紧张,你想想办法,不要给他做饭,还是不要给他零花钱。”
“他有钱,他有些收入就在办公室里放着,钱上卡不住他。”
“那也没什么,首要的是你不要怕他。你现在占理,就是离了婚也不怕啥。”
丁兰知道赵淑华在闹离婚,每天和孙二桃厮混在一起。半夜不睡,早晨不起,除了吃喝就是跳舞逛街,混混沌沌,也不说领证结婚,就那么稀里糊涂的混日子。
所以她说起离婚来,满不在乎,而她丁兰不行啊,她认为女人一旦要是离了婚就不值钱了,想再重找一个体贴自己的男人很不容易,从哪儿找?
像她这年近四十岁的女人,只能找同她年龄一般或者大一些的男人,年龄小的肯定不愿找她,年龄大的,五十来岁,六十来岁的男人。
她还不愿意,觉得对方比自己大十来岁,心里不舒服,可年龄相仿的人从哪儿找呢?唉,她叹了口气,半晌不说话。
“喂,你咋不吭声了?”赵淑华在手机那头嚷嚷,“发什么憨了?别想不开,你那个病我认为肯定能看好,到时再找个男人,离了李本天就不活了?
现在我就能帮你联系一个,先联系上,咱们边谈边看病。明天晚上,你和我到红玫瑰舞厅,我给你推荐一个。他李本天能找小情人,你也能找个情人,气气他。”
丁兰忙说:“不行,我做不来。咱们别说了,明天再聊吧。我要关机了,对不起。淑华”
“明天你去不去呀?”
“不去,我关机了。”丁兰切断手机,抬头看了眼墙上挂的时钟,已凌晨两点。
到这时李本天还不回来,就是不回来了。这家伙是成心和我过不去,没良心东西,心眼坏了。当初她找李本天,是父亲极力主张的,说找个退伍军人好。
军人的基础素质好,体质好,工作能力强,过几年就能提上去。她知道父亲是当过兵的人,跟军人有感情。她也看到李本天长的排排场场就同意了。那阵李本天正为工作安排搞得焦头烂额,找不下一个合适单位。
和她见面后,她给父亲说了李本天的工作安排情况。果然没几年当了科长,可这人太没良心,当了个破科长,就跟别的女人胡来,真气人!我该怎么收拾他?
在丁兰胡思乱想的时候,她想起另一位密友李玉。李玉在一家夜间超市工作,应该没休息,这个时间段,工作也不忙。
正想着,她的手机嘟嘟响,看来电显示,恰是李玉的电话,她按通手机,李玉在手机中亲热的问:“兰兰,你的电话真难打,这么长时间都叫不通,你在同谁说话了?”
“跟淑华说。”
“哦,原来如此,刚才淑华给我来电话,说你在舞厅抓住李本天的把柄了,闹了一场,究竟是怎么回事,你和我说一说。”
丁兰就把在舞厅中打李本天的事说了一遍,最后问:“你看我现在怎么办啊?是离婚还是宽恕了他?”
李玉说:“你先别着急上火,和他好好谈一谈,看看他在想什么,是什么态度。
你再想想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,想想你们两口子在哪些地方做的不合适,不协调。”
“和谐啊。”丁兰心里底虚,口是心非地说。其实她在生了乐乐之后,就自顾自抱着儿子睡,给他个后脊背,不理他,气得李本天直叫唤。
她和他在半夜三更吵架都是因为这件事引起的。但这种事,能给别人说吗?。
手机里传来李玉的问询:“如果他偶然一下沾花惹草,还能悔改,你就原谅了他,不要把事情弄大;如果他有了二心,是想再找个小的,那就没办法了。”
听到密友亲切的分析,丁兰的眼泪扑簌簌的又一次掉下来,她哽咽着声音:“可他现在还没回来,我咋和他谈呢?”
“不要急,等一等,今晚他不回来,还有明天,明天不回来,还有后天,他总要回家的。”
“我还能这样等他,这么被动?”丁兰含着泪,气呼呼的说。
“那你说咋办?”
“明天我去单位找他,到韩叔那里告他一状,让韩叔狠狠的教训他,他就老实了。”
“别去找韩局长。你去告状,韩局长肯定会骂他,把事情就弄大了。单位的人就都知道了,会影响他工作,影响他的前途。”
“给他前途?”丁兰生着气骂:“我不能再帮他。才当了一个小科长就美的玩女人,不知天高地厚,要是当了局长还不知咋胡闹呢!”
“不要这样,兰兰。男女的事都是大事,稍一不慎就会出问题,有很多人的一生就是毁在这男女问题上。
你千万不要冒失,他毕竟是你儿子的爸爸,从儿子那个角度你也要冷静思考,不能去局里告他。”
李玉的话似一壶清水滋润了丁兰的心,把她心里的火一下子压了下去,是呐,儿子都九岁了,正在成长,以后长大了要是听到他爸爸的这件丑事,会被别人笑话,不是伤他的自尊心吗。
她不吭声了,心里翻腾的十分难受。儿子的前途重要呐,可不到找韩叔告他一状心里又不甘,矛盾的心情折磨着她。过了一会儿,她对李玉说:“咱们以后再说。”
关掉手机。她静下心来,细细想了一会儿,觉得还是儿子的前途重要,为了儿子不和他计较了。
他要是有悔改之心,就饶了他,他要是不悔改,我就去找韩叔告他,让他尝尝胡来的后果,在焦虑的思考中她迷迷糊糊的靠在沙发上睡着。
第二天中午,李本天没回家。晚上丁兰给李本天打电话,手机光响不接。气得她咬牙切齿的骂:“你等着!”她认为李本天又和她别上劲,我就是不回家,你能把我咋办?
隔天早晨,她到文化宫骑上存在那儿的电动自行车,风一般的奔向李本天的工作单位市。
五层大楼。李本田的办公室土地综合管理科在一楼,他是这个科的科长,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。
此时他正清扫办公室。
大前天晚上,丁兰到舞厅大闹,搅了他和舞伴林小雪的好事,当时他恼火的很,心想,她怎么知道的?
肯定是有人密告她。这件事让他十分不安,回了家和丁兰怎么说呀?让她抓了个正着,他一点辩解回旋的余地都没有,她肯定要和他大闹。她那脾气太暴躁,什么家具都敢拿起来打,什么话都能骂出来。
她的嘴伶牙俐齿,比播音员说话还快。如果要是她和他打起来,他一拳就能把她打得爬不起来。
可是他不敢打呀。她的家庭背景太强大,她爸爸在部队当过团长,转业到地方是环保局长,跟他顶头上司,国土局的局长是老战友,关系很亲密。
她的哥哥丁建在派出所当所长,他要是打了她,她哥哥肯定会开警车来抓他。打人是犯法的,打老婆也是犯法。他一个指头都不敢动她一下。而她,却能出手打他。女人打男人没事,男人打女人可不行。
女人打男人虽然打不成个什么,顶多就是脸上让她抓几道子挨几耳光。可问题是她要是问起林小雪,他怎么解释?
这个问题实在是不好回答,现在,只有在外面躲一躲好。等她火气消了再说。他住在办公室了。
他和林小雪的相识是在半年前。春节长假期间,科里的小马和女友小贾请他吃饭。三人酒足饭饱之后,在小贾的建议下来到舞厅跳舞。
他不会跳,仅仅是在局里面跟女同事学过几次,能走几步,步子不熟。
他座位上观看。小贾见他坐着,便打电话请来同学林小雪陪他跳舞。林小雪见他不会跳,就热情耐心的教他。
林小雪长的相貌清秀,身材苗条。让他看着十分喜欢,劲头十足的学了一下午。他觉得搂着林小雪似搂着仙子一般柔若无骨,美轮美奂,舒畅惬意。
而搂着丁兰跟搂着泥胎一样,僵硬死板,机械乏味,跟嚼蜡一样没什么感觉。怪不得人们说家花不如野花香。这个野花就是比家花香呐。
那天傍晚,他请她们在云山饭店吃了一顿,临分手时,他塞给林小雪一张华联超市的200元购物卡。
他身上经常带着超市购物卡,是关系户在年前赠送的。
每年都能得到十几张千元和万元的购物卡,除一部分交给老婆丁兰,自己留下几张,回老家前买些年货孝敬父母。
林小雪接过卡,十分高兴,娇柔的说,谢谢大哥.看着林小雪那喜欢温顺的模样,他心里舒畅极了,豪爽地说,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尽管开口,我一定尽力而为。
他觉得和一个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在一块,自己仿佛也年轻了几岁。
隔天晚上,林小雪打电话邀他跳舞,意思是答谢他的请客。他哄丁兰去战友家搓麻将,开着车去了舞厅,和林小雪玩了两个小时,愉快万分。
过了几天,他到医院看望同事。在门诊部楼前遇见林小雪从楼里往外急匆匆的走。他拦住她问,你来这儿做啥?她一看到他,黯淡的眼睛立刻闪出两道明亮的光。
告他,她妈得了子宫肌瘤,要在医院做手术,准备回去借钱。李大哥你有钱吗?能借给我一些么?
林小雪向他借钱。他大方豪爽的说,你要多少?林小雪说,两万。
他说,就借这么点?林小雪说,这么点我家也没有。我爸住院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花光,还欠着外债。他听后心里生出一丝怜悯。
后来他了解到,林小雪的父亲已病故,母亲是纺织厂下岗女工,只有一些微薄的下岗生活费,没有积蓄。
当时,他从银行取了三万块,多给了林小雪一万,告她不要去打工,在家伺候母亲。林小雪感动的问,大哥,你什么时候用钱?我还你。他说,不用还,我有。
他的工资有多少?五千多元而已,可他的外快收入可不少。有些求他的人除了送购物卡,还有拿包装现金来送的。
另外还有,如他去参加一个房地产商人的开盘仪式,肯定会送他一个大红包。逢年过节,还有人给他送银行卡,五万十万的都有,这钱是不能说的。
从那以后,林小雪成了他的情人。当时他想,多给了一万,她成了他的情人。如果是借给她两万,也就是个朋友啦。
他为他会做事而他之所以不回家,不接丁兰的电话,就是在考虑离婚以后的事。
他给林小雪打了几次电话,她不和他见面,说是从外地回来一个同学,她要陪同学玩几天。什么同学使她不和他见面?很让李本天费心思。
国土局工作人员有个习惯,上了班先打开水,每层楼都在卫生间门口安着一台热水器。
李本天清扫完办公室卫生,提着得意。
之后,他时常把丁兰和林小雪对比,丁兰是一丈青,脾气暴燥,性情不好,没女人味。林小雪是貂蝉,温柔敦厚,美艳绝伦,充满芳香,妙得很。
但他也想到,如果这件事一旦要是被丁兰发现,她肯定和他大闹。他就和她离婚,娶林小雪,虽说年龄上有些悬殊,让他心里不踏实。
但他还是想娶她,这两天暖瓶到卫生间旁打水。他站在检验科秘书小苗身后等着。
小苗灌满水后准备离去,不经意看了李本天一眼,忽然“咦”了声,盯住他的脸问:“李科长,你脸上怎么了?”
“怎么啦?”李本天摸了下脸,顿时感到浑身不自在。他脸上还留着前天晚上被丁兰抓的几道痕迹,可这不能说。他只能掩饰:“昨晚喝多了,在墙上蹭了下。”
“是吗?可你的脸这边有两道,那边也有两道。在墙上蹭,还这边蹭一下,那边蹭一下?”小苗直来直去,刨根问底,。
李本天被问的张口结舌难以回答。他心里急得直骂,这个丫头片子一直问啥了?编个什么理由糊弄她。
没想到对面站了个检验科长老高。老高呵呵的笑:“那是被老婆抓的,没问题,谁有胆量敢破咱们老李的相。不是老婆就是小三。”
李本天反应很快,马上回击:“你的脸是不是被老婆抓过?”
“是啊,抓过,就你这个样。”老高快嘴快舌,说罢,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。
李本天还想编个说法辩解,一时却找不下,心里直发牢骚,这个老高是哪壶不开提哪壶,真让人下不了台。
老高彷佛是说到兴头上,嘴舌停不住,继续叨叨:“我老婆那爪子可厉害了。去年她和我吵架,我回了几句,她上来就在我脸上抓了两把,又揪住我的耳朵拧,问我以后骂不骂人。
我又不是骂她,我只是说话爱带个把子,她就说我骂她,冤不冤呢。”这和他去年跟丁兰吵架是一个版本。
而小苗呢,仰起脸笑眯眯的看李本天的耳朵,彷佛要在那里发现什么秘密,弄得他很不自在,但他还是抓住机会,向老高发起攻击:“活该。”
两人正说笑着,门厅正中传来一句严厉的声音:“李本天,你过来!”
丁兰来了。
原创文章,作者:橘子柚子小果子,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livip.net/149456.html